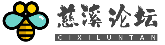四五年时间过去了,永州司马柳宗元仍然念念不忘他的人生的辉煌顶峰,而今则处在相去甚远的落魄境地,这随之带来的落差感,形成某种心灵的牢笼,让他难以解脱。
在这种时候,往人迹罕至的地点旅行,往往是一个消化郁闷,开拓心胸的办法。在他810年所写的名篇《始得西山宴游记》这样写道:“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其隙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
《始得西山宴游记》提到一个地方“染溪”,又叫“冉溪”。位于今湖南省永州市芝山区河西,东流入潇水(今湖南省道县北)。冉溪是一个好地方,柳宗元显然是看上了这块地方,成为他寄情山水的一个“根据地”。
他在诗作《冉溪》中写道:“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缧囚终老无余事,愿卜湘西冉溪地。却学寿张樊敬侯(东汉他樊重,汉光武帝的内戚,称樊敬侯),种漆南园待成器。”
这还不够尽兴。于是自作主张地把冉溪改成了所谓“愚溪”,因此诞生了《八愚诗》以及这篇《愚溪诗序》,《八愚诗》已经失传,《愚溪诗序》则颇有名气,被选入《古文观止》等古文读本。这样一个改溪名的举动,很大程度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窥探柳宗元精神世界的窗口。
柳宗元不是无缘无故该一条溪的名字的。《愚溪诗序》的开头便道出了缘由:“灌水之阳有溪焉,东流入于潇水。或曰:冉氏尝居也,故姓是溪为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谓之染溪。予以愚触罪,谪潇水上。爱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绝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余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犹龂龂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为愚溪。”(《愚溪诗序》)
他的这段话主要有两个理由:第一个是愚溪以前有两个名字,即冉溪和染溪,但是在当地人之中仍然是争论未定的。第二个是他把家安在这里,其根源是“以愚触罪”,加上“古有愚公谷”。
柳宗元作为一个新居民去修改当地的溪名,是很鲁莽的。当然,他在文中也没有说它的这个名字有没有被当地居民接受,很可能就是他的“自娱自乐”而已,所以也就没什么要紧。
但是,这还是说明柳宗元的地位是要比当地的居民要高的,所以他敢去改溪名,如此随心所欲,让人想到一个游山玩水的帝王,一言一行就改变了一个地方的历史。
这里还提到一个典故“愚公谷”,并与愚溪形成对比,透过这个典故,可以看到柳宗元内心隐藏的骄傲。
“愚公谷”典故出自西汉刘向《书苑》第二十卷:齐桓公出猎,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见一老公而问之曰:“是为何谷?”对曰:“为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对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视公之仪状,非愚人也,何为以公名之?”对曰:“臣请陈之:臣故畜牸牛,生子而大,卖之而买驹。少年曰:‘牛不能生马。’遂持驹去。傍邻闻之,以臣为愚,故名此谷为愚公之谷。”桓公曰:“公诚愚矣!夫何为而与之?” 桓公遂归。明日朝,以告管仲 。管仲正衿再拜曰:“此夷吾之过也。使尧在上,咎繇为理,安有取人之驹者乎?若有见暴如是叟者,又必不与也。公知狱讼之不正,故与之耳。请退而修政。”
核心的内容是:有个老人家养了一头母牛,生下小牛长大卖掉小牛而买来小马。一个少年看到说:“牛不能生马”,强行把小马牵走了。于是他居谷被邻人称为“愚公之谷”。齐桓公出外打猎的时候知道了这件事,然后把老人家的愚蠢说给管仲听,管仲认为这个老人家是大智若愚的,因为他知道当今世上愚昧混乱且很难保护他,所以别人借口抢走他的小马也没有去阻挡。
柳宗元认为自己的“愚溪”是接近这位老人家的“愚人谷”的。那么,他自己难道不就是他那个时代的老人家呢?
我们不需要快速下判断。因为柳宗元显然不满足“愚人谷”的典故的内涵,他买下了居住地附近的丘、泉、沟,都加上愚字,即愚丘、愚泉、愚沟,并且还自己生造出“愚池”、“愚堂”、“愚亭”、“愚岛”等地,以至于所有的“嘉木异石”,构建出了一个独属于柳宗元自己的“愚世界”。
即:“愚溪之上,买小丘,为愚丘。自愚丘东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买居之,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盖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为愚沟。遂负土累石,塞其隘,为愚池。愚池之东为愚堂。其南为愚亭。池之中为愚岛。嘉木异石错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予故,咸以愚辱焉。”(《愚溪诗序》)
柳宗元自己认为是“以愚辱焉”,也就是是用“愚”侮辱了这一片地域。但是,我们很难不觉得这是一种潇洒快意,无所拘束,甚至胆大妄为。判断一个人是否拥有顶级权利,可以从他是否能去命名事物来看,中国古代帝王“赐名”“赐姓”“赐地名”等历史,以及福柯所谓的“话语权”便是这个道理。
当然,柳宗元的理由似乎是蛮合情合理的。他说:“夫水,智者乐也。今是溪独见辱于愚,何哉?盖其流甚下,不可以溉灌。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浅狭,蛟龙不屑,不能兴云雨,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予,然则虽辱而愚之,可也。”(《愚溪诗序》)
刚才的行文他是锋芒毕露的,现在的行文是谨慎的。他认为愚溪的水道很低,不能用来灌溉田地。水流很急有很多石头,船舶也进不来。幽深浅窄,蛟龙更不可能在此兴云雨,所以对于世界是没有好处的。就像他一样,所以用愚溪来称呼这条溪也是可行的。
这当然是一种充满愁怨的说辞,溪水怎么可能对世界没有好处呢,对岸边的花草树木总有用吧,对于玩耍的孩子总有用吧,而他的存在怎么可能对世界没有好处?历史证明,他的存在是伟大的。
柳宗元执着于解释这条溪可以如此命名,以及他拥有这样的命名权。相比前者,柳宗元下面这个思考着实令人震撼。他说:“宁武子‘邦无道则愚’,智而为愚者也;颜子‘终日不违如愚’,睿而为愚者也。皆不得为真愚。今予遭有道而违于理,悖于事,故凡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则天下莫能争是溪,予得专而名焉。”(《愚溪诗序》)
这里涉及两个典故。“宁武子‘邦无道则愚’”出自《论语·公冶长》记载:“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邢昺疏:“若遇邦国有道,则显其知谋;若遇无道,则韬藏其知而佯愚。”宁武子是春秋卫大夫宁俞,谥武子。一般以宁武子为国家有道则发挥才华、无道则装愚保存自己的政治家的典型。
另一个“颜子‘终日不违如愚’”出自《论语·为政》记载,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也就是说颜回从来不提与老师不同的意见,看起来很愚蠢,但实际上是默默思考,其私下言论中已经对老师的话有所发挥了。
柳宗元说这两个典型都不是真愚,他才是真愚。因为他在政治清明的时候却做出与事理相悖的事情,没有像他这般愚蠢的人了。所以他拥有这条溪的命名权。
粗看这似乎是一种对朝廷讽刺。清人何义门《义门读书记》说:“词意殊怨愤不逊,然不露一迹。”认为柳宗元是拐着弯骂朝廷的。
但是,我们能不能认为柳宗元这句话也是有道理的呢?因为它面对的是被后世史家称之为“元和中兴”的初期,贬抑他的皇帝是一个安史之乱以来的拨乱反正的唐宪宗。尽管元和中兴的含金量有待商榷,但确实可能使得那个时代出现了柳宗元所谓“有道”的现象。
面对这样的现象,一个诚实正直的政治家没法不注意到,更不可能不给予公正的评价,即使它可能与自己所处的立场有悖,甚至跟自己有仇。柳宗元应该是有这样的自觉的,所以他写下这句话也是一种严肃的反问。
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里说的那句话的意思:“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籍,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是不是常常会敲击他的内心呢?我想是会的。如果他没有选择激进的改革路径,是不是就不“违于理,悖于事”了?
其实,柳宗元已经做过那个时代最伟大,最出格的事情了,即使没有完全成功,也应该满足了。毕竟他只是政治上被唐宪宗抛弃。在经济上仍然可以领取俸禄。还有余钱和余暇游山玩水。比起大多数的处境都要好得多。况且他们的主要主张是被唐宪宗践行了的。
当然,这是我们的“马后炮”。所谓“当局者迷”。对于无法处理的纷杂世事,中国文人们的一般的处理方式是沉浸于山水、以文墨自慰、以及追求一种出世的精神境界。
这也是柳宗元在最后所写到的主要内容:“溪虽莫利于世,而善鉴万类,清莹秀澈,锵鸣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乐而不能去也。予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以愚辞歌愚溪,则茫然而不违,昏然而同归,超鸿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于是作《八愚诗》,纪于溪石上。”(《愚溪诗序》)
当然这也并不意味就解脱了,与之而来的也会有新的麻烦。比如“寂寥而莫我知也”这句话,说的是天地之间没有人能够理解他。人生的真谛或许就是你永远都无法真正摆脱人生的负重。
想来,柳宗元“不合于俗”还能“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通过虚构审美世界来获得精神栖息地和反抗的力量。但我们大多数俗人遇到“不合于俗”之时,恐怕连“以文墨自慰”也不能。无穷的沉默和顺从啊,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