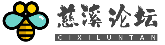我从一九九一年九月认识倪庆饩先生,于今已二十九个年头,不算太长,可也不算太短。在这段时间里,我前前后后,写了长短不一的几篇文章,或是评介倪老师翻译的书,或是记述他的生平或和他有关的故事,总共大概有八篇:
一、《从柳无忌开始》,评倪译柳无忌著《中国文学新论》,发表于《博览群书》1995年第5期;二、《遥望小泉八云》,评《小泉八云散文选》,发表于《博览群书》1996年第5期;三、《译者倪庆饩》,评《高尔斯华绥散文选》《卢卡斯散文选》等,见于《羊城晚报》2002年8月1日;四、《有关柳无忌先生的书缘旧事——纪念柳无忌先生百年诞辰》,发表于《温故》第十一辑,2008年4月;五、《英国散文的伟大传统》,评戴维斯《诗人漫游记 文坛琐忆》,赫德逊的《鸟和人》,多萝西·华兹华斯的《苏格兰旅游回忆》和《格拉斯米尔日记》,发表于《读书》2012年第5期;六、《万里文缘 百年穿越——赫德逊〈鸟和人〉及倪译四种》,见于《人民政协报》2012年2月13日;七、《知识如水,智慧如光》,评赫胥黎《水滴的音乐》,发表于《光明日报》2017年3月28日;八、《倪庆饩》,发表于《随笔》2017年第5期。
其中,四和八的篇幅稍长,都有一万字。不过,这些文章,都是倪老师在世时写的。他去年过世之后,我并未写什么。最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要再版倪老师的三本书,嘱我写几句。现在再写,就是第九篇了。我希望,这篇文章,能把对倪老师的思念写尽。
二
为了让不太了解倪老师的读者对他有个初步的了解,现在,我把手头儿现有的倪老师翻译的书,按出版时间列在下面。后期有不少书,其实译出的时间比出版时间要早十年或者更早。
1.《英国浪漫派诗选》,柳无忌、张镜潭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2月,倪庆饩译雪莱、济慈诗
2.《史蒂文生游记选》,[英]史蒂文生著,倪庆饩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年3月,17万字
3.《赫德逊散文选》,[英]威廉·亨利·赫德逊著,林荇(倪庆饩)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7月,16万字
4.《中国文学新论》,[美]柳无忌著,倪庆饩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20万字
5.《小泉八云散文选》,[英]小泉八云著,孟修(倪庆饩)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17万字
6.《驱驴旅行记》,[英]史蒂文生著,倪庆饩译,花山文艺出版社,1995年11月,15万字
7.《巴兰特雷公子》(小说),[英]史蒂文生著,周永启、倪庆饩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12月,18万字
8.《普里斯特利散文选》,[英]J.B.普里斯特利著,林荇(倪庆饩)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12月,15万字
9.《一个超级流浪汉的自述》,[英]威廉·亨利·戴维斯著,倪庆饩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2月,18万字
10.《大海如镜》,[英]约·康拉德著,倪庆饩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4月,14万字
11.《高尔斯华绥散文选》,[英]高尔斯华绥著,倪庆饩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16万字
12.《卢卡斯散文选》,[英]卢卡斯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4月,16万字
13.《鸟界探奇》,[英]威廉·亨利·赫德逊著,倪庆饩译,花城出版社,2003年4月,16万字
14.《我与飞鸟》,[加]杰克·迈纳尔著,倪庆饩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4月,15万字
15.《爱默生日记精华》,[美]爱默生著,勃里斯·佩里编,倪庆饩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1月,14万字
16.《绿厦》(小说),[英]威廉·亨利·赫德逊著,倪庆饩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1月,18万字
17.《诗人漫游记 文坛琐忆》,[英]威廉·亨利·戴维斯著,倪庆饩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14万字
18.《鸟和人》,[英]威廉·亨利·赫德逊著,倪庆饩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13万字
19.《苏格兰旅游回忆》,[英]多萝西·华兹华斯著,倪庆饩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15万字
20.《格拉斯米尔日记》,[英]多萝西·华兹华斯著,倪庆饩译,花城出版社,2011年8月,17万字
21.《水滴的音乐》,[英]阿尔多斯·赫胥黎著,倪庆饩译,花城出版社,2016年5月,20万字
22.《海港集》,[英]希莱尔·贝洛克著,倪庆饩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17年5月,8.7万字
23.《罗马行》,[英]希莱尔·贝洛克著,倪庆饩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17年5月,12.5万字
24.《英国近现代散文选》,[英]威廉·亨利·赫德逊等著,倪庆饩译,河南大学出版社,约15万字,2019年即出
25.《少年行》,[美]华尔纳著,倪庆饩译,河南大学出版社,约15万字,2019年即出
26.《伦敦的鸟》,[英]威廉·亨利·赫德逊著,手稿,约16万字,未出版
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散文热席卷全国。天津的百花文艺出版社领一时之风骚。当年,他们出了两套大型散文丛书,一是中国的,叫“百花散文书系”,包括古代、现代和当代。还有一个是外国的,叫“外国名家散文丛书”,两套丛书影响都很大。一九九一年时,就已推出第一辑十种,包括张守仁译的屠格涅夫,叶渭渠译的川端康成,叶廷芳译的卡夫卡,戴骢译的蒲宁,还有《聂鲁达散文选》《米什莱散文选》等,第一辑中,《史蒂文生游记选》即为倪庆饩译。由此开始,百花每年推出十种中国散文,十种外国散文。百花主持此事的副总编谢大光,每年请倪老师翻译一本,连续若干年:第二辑《赫德逊散文选》,第三辑《小泉八云散文选》,第四辑《普里斯特利散文选》,而卢卡斯和高尔斯华绥两本,是在同一辑里一齐出版的,可见当年译者倪庆饩的热情与多产。
倪老师翻译这些作品,从选目开始,就有讲究。他不是抓着什么译什么,而是研究文学史,查找《牛津文学词典》等工具书,专找那些有定评的大作家的作品,而且是没有中译本的。所以,几十年下来,把倪译作品集中放到一起看,就会看出其独特价值:一是系统性,二是名家经典,三是填补空白,四是译文质量高。他觉得,有那么多一流作品还没有被翻译介绍到中国来,完全没必要扎堆去重复翻译那些大家熟知的作品,尽管那些作品会更卖钱。倪老师曾对我不止一次说过,与其自己创作二流甚至三流的所谓作品,不如把世界一流的作品翻译过来,更有意义。如果没有倪庆饩的译介,这些英美一流作家的散文经典,一般中国读者很有可能至今都不会读到。
倪老师已经翻译的作品,以英美散文为主,其中,又以英国散文最为集中。这个“美”,不仅指美国,也指北美,也就包括加拿大。这其中,又有四本关于鸟类的书,自然引人注目。译者大概是真正体会到了赫德逊、迈纳尔对鸟类的那种感情。在大自然中,大多数鸟对人是无害的,其中许多还是有益的。又因为大多数鸟都很美,有观赏性,而且能飞,就比草木更多了几分灵动,与走兽比,则更多了轻盈与超凡脱俗的气质。鸟,不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自古就寄托了人类飞翔的梦想。大雁、夜鹰、红雀、银鸥,她们是串联草木、湖泊和天空的朋友,是森林的精灵,也是天空中飞翔的天使。倪老师早年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说,他所有的译作都贯彻一个宗旨,“即追求自然与人的精神的sublime”。这sublime,是崇高,是超凡,是升华,是向上的飞升。显然,没有什么比美丽的鸟儿更能寄托这种追求了。
《我与飞鸟》的作者迈纳尔(1865~1944)是加拿大的一位博物学家,也是一位严谨的科学家。作者在书中记叙了他建立金斯维尔鸟类保护区的过程,包括一些技术的细节。全书的重点是写大雁和野鸭这两种候鸟的几章,从营巢、交配、产卵、孵化、驯养,以至套环、迁徙等过程都有详细的记载。译者认为,这不但是迈纳尔创造性的经验,也是极其有价值的科学实验记录,比如现在已搞清楚的它们的迁徙路线,它们营巢与交配的方式。“他一度是以一个猎人的眼光去看大自然中的生物,对他来说,它们只是一种猎物,可供美餐,也有经济价值,但他后来渐渐认识到鸟类的可爱,使他的自然观有了根本的转变,结合宗教尊重生命的观点,从猎人转变为自然保护者,这个过程以及其间发生的故事不但对广大读者具有积极的教育意义,也读来兴趣盎然。”
《鸟与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2019年6月
而对另外两本书《鸟界探奇》《鸟和人》的作者威廉·亨利·赫德逊,译者倪庆饩是这样评论的:
赫德逊写的是文学的散文而不是科学的鸟类志。他写鸟当然要写鸟的形态,生活习性,如觅食、育雏、迁徙,等等,这通常是我们在鸟类学的专著和科普作品中也可以读到的。赫德逊的散文与这类自然科学性的著作不同的是,他从来不是孤立地写鸟,而首先是把鸟和它们生存的自然环境结合在一起,把我们带到许多风景优美的地方,如森林、海滨、郊野,使我们接触到许多如画的景色,因而我们看到的鸟不是博物馆中的标本而是鲜活的野生鸟类,随着他的笔触我们几乎游历了英国西南部的整个地方,如索姆塞特郡、汉普郡、威尔特郡、苏菜郡、苏塞克斯郡等,例如本书中的萨维尔纳克森林就在威尔特郡,他描写那里的古老参天的山毛榉林和在那里生息的成千上万的鸦科鸟类,在作者的笔下,使这种平时不怎么可爱的飞鸟也带上了诗情画意。这决定了赫氏散文的一个根本特点,即他往往是以审美的眼光而不仅是以科学的眼光来看鸟类世界。
同样鲜明的是,在赫德逊的笔下,鸟类不仅与它们生活的自然环境不能分割,同时也与它们生活的人文环境不能分割。他写鸟和人以至他们家庭相关的故事,许多飞鸟生存的教堂、墓园、旧宅等建筑物和古迹,穿插着许多咏鸟的诗歌以及有关鸟的传说,使读者明显地感觉鸟和人的密切关系。
批评家爱德华·加尔奈特指出:赫氏作品令人神往的地方是他从不把大自然的生命跟人的生活截然分开。读者如果阅读了《鸟和人》或赫德逊的其他作品,都会深深体会到这一点。从这两个方面看,赫德逊的散文本质上可以说是游记,《鸟和人》也是如此,只是这是一种融合了科普、博物学的游记,或者说是有着深深的人文情怀的博物学美文。《鸟界探奇》还讲了许多鸟和人的故事,赫德逊说:“对待飞鸟一定要顺从他们的天性,鸟也像人一样,自由超过一切。”译者则从中读出,这些故事使赫氏的书超越了科普读物的局限,具有鲜明的人文意义。
一九○一年,《鸟和人》出版。一九三五年,中国著名作家李广田在他的《画廊集》中,专文写到赫德逊和他的这本书(《何德森及其著书》)。——他们那一代作家,与世界文学声气相通。《画廊集》一九三六年三月在商务印书馆初版,属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之一。又过了六十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倪庆饩教授根据一九一五年第二版译出《鸟和人》。因为机缘巧合,出版《李广田全集》的云南人民出版社,想找合适的译者来翻译此书。他们通过李广田的女儿,问到我。这当然是个惊喜。《鸟和人》,还有《苏格兰旅游回忆》和《诗人漫游记 文坛琐忆》,那厚厚的几大摞手写的稿子,一直被裹在几个大文件袋中,寂寞地躺在译者的书桌里,这次终于等来了知音。二○一一年,《鸟和人》中文版出版。经过几代人,跨越万里,穿越百年,这部散文经典化身汉语在东方世界出版,赫德逊洒脱的文笔,博大的情怀,通过优美的汉语译笔呈现了出来。这当然令人感慨。这既是中国读者之幸,可以说也是赫德逊之幸和英国文学之幸。
三
如果从一九四七年倪庆饩翻译发表希曼斯夫人的诗《春之呼声》算起,他的翻译生涯长达七十年。那时的倪庆饩还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一名学生。倪老师多年后能翻译英美那些大作家的作品,而且,对这个事情常年保持热情,与他当年在圣约翰大学所受教育关系很大。在圣约翰的那几年,倪庆饩接受了最好的英语教育,特别是古典英语熏陶多年。他直接听得是王文显、司徒月兰等人的课。除了语言学习,在英语系,他上得最多的是文学课,课程按专题设立,如莎士比亚专题课、英诗专题课、小说专题课等,这使倪庆饩系统、深入地了解了英语语言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作品。倪老师曾说过,“司徒月兰教过我的英语基础课,她的英语发音挺好听的,讲得地道而流利。王文显教的是莎士比亚专题课,他讲课不苟言笑,却有一种温文尔雅。而英诗、小说这些专题都是外籍教师教,他们的英语素养就不用说了,真是原汁原味”。
倪老师的外语修养,不限于英语。他曾对我讲,俄语、德语,他也能读,日语,他也粗通,因为他上小学中学的时候,就被迫学了日语。这些,都为他日后的翻译提供了条件。一些原著中涉及的俄语、日语方面的问题,他都能直接解决。
大学毕业后,倪庆饩曾在北京待过一段,在某对外文化交流部门短暂任职。后因患肺病而被迫离职回湖南老家养病。一九五三年,他到湖南师范学院任教,开始是在中文系教外国文学。十余年的教学与研究,让他“打通”了欧洲文学史的“脉络”,这对文学翻译工作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他当时在教学之余,也偶尔搞一些翻译,但他自称都是“零碎不成规模”。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倪老师调到南开大学外文系任教。八十年代以后,开始了他大规模系统的翻译。
他的翻译,完全手工。第一遍用铅笔或蓝色圆珠笔初译,写出草稿,会写得较乱,改得密密麻麻;然后誊清,对着原书,用红笔再修改一遍;然后再用钢笔誊清。如是,至少三遍。最后一遍字会比较工整,因为是要出手的东西了。一部十几万字的书,相当于他要至少抄写四五十万字。这几十摞文稿,总计近四百万字,都是他一笔一画,一字一句,一遍一遍地写,誊,精心打磨出来的。
正常状态下,第一遍初译,倪老师平均每天能译两三千字。如果身体状态好,其他各方面又没有什么牵扯,原作又不是很难,那么,一部十五万字的书,两个月左右可以完成初稿。但多年以来,大多数时候,一部书的翻译时间要更长一些。
不过,作为译者,碰到赫德逊《鸟界探奇》这样的书,仍然意味着一种挑战。这些关于鸟的散文、游记,内容广涉自然,博物学、动物植物方面的专业名词,对译者也是陌生的领域。他一个老人,就跑图书馆,一个词一个词地查词典,找各种工具书来解决。这些,都需要大量的时间。
他愿意花这么大的力气来译这些书,当年在我看来,实在有点儿不太理解,因为书的内容与我们实在有点儿远,与我们的实际生活搭不上边儿,又不被我们以前的知识教育所关注,于我们的世俗谋生更是一点儿用处没有。而这其中,又数赫德逊写鸟的书,更让我觉得没用——想想,自己是多么的庸俗和目光短浅。但倪老师特别有热情。这主要是因为,他真的是喜欢赫德逊的散文,喜欢赫德逊这些关于鸟的描述和审美。这应该是与他内心的某些方面十分契合。他在赫德逊的文字中,在迈纳尔的文字中,在他们对鸟儿的生活的描述中,找到了一种不同于凡世的别样的生活。那也许是他向往的。他一辈子在尘世中躲避,挣扎,沉默,小心翼翼,守着自己的一份善良与职业尊严。而在这些作品中,他能找到自由与美,在那漫长的翻译工作中,他能感到自如与自信,在这种自如与自信中,他感到了力量。那些年,他曾不止一次,当面和我说起他翻译这些书的不易,要查各种工具书,为了一个名词,都要花费很多时间。但同时,我又能在他的诉苦中,感到他的一种满足。他是在自讨苦吃,但是,他在这苦中找到了只有他一个人享受的甜。他最开心的时候,就是他拿到新出版的书的那天。他在这辛勤的工作中,得到了莫大的乐趣。
倪老师倾注到译作中的心血和功力,完全地体现在译文、注释和译后记中。注释,体现了译者的水平和认真。译作中,对原著涉及的外国人名、地名、事件,西方文化的背景等都做了注解,对理解译文有相当帮助,注所当注,精到、简洁、要言不繁。他所写的序言或译后记,本身就是一篇篇文艺随笔,信息丰富,评论作家作品简洁、中肯、有见地。读者可以从赫德逊《鸟和人》《鸟界探奇》和迈纳尔《我与飞鸟》的译后记中,印证我的观点。
虽然倪老师所翻译的,都是自己所喜爱的作家的作品,但他并非对其一味赞美,对其得失,他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比如,他对卢卡斯的看法是:“他写得太多,有时近于滥,文字推敲不够,算不得文体家,但是当他写得最好的时候,在英国现代散文史上占有一席地位是毫无疑问的。”而对于自己十分推崇的小泉八云(原名拉甫卡迪沃·赫恩),译者认为:“我并没有得出结论说赫恩的作品都是精华,他的作品往往不平衡,即使一篇之中也存在这种情况,由于他标榜搜奇猎异,因此走向极端,谈狐说鬼,信以为真,这样我就根据我自己的看法有所取舍。”他对作家的评价,都是从整个文学史着眼,把每个作家定位,三言两语,评价精当。比如他认为,史蒂文生“作为一个苏格兰人,他把英格兰与苏格兰关系上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作为他的历史小说的背景,在这方面,他的贡献堪与司各特相提并论。奠定他在英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的,还有他的散文。他是英国散文的随笔大师之一,英国文学的研究者公认他是英国文学最杰出的文体家之一”。他为每部作品写的译后记,都是一篇精辟的文学评论,概括全面,持论中正,揭示这个作家的最有价值的精华;语言简洁、优美。译者倪庆饩,不止是不为流俗所动的了不起的翻译家,还是一位有见识的文学史家。下面这段话,不仅为多萝西·华兹华斯在文学史上标出了一个位置,我以为还可以作为英国散文史的一个高度概括,很有参考价值:
在英国文学史上散文的发展,相对来说,较诗歌、戏剧、小说滞后。如果英国的散文以16世纪培根的哲理随笔在文学史上初露异彩,从而构成第一个里程碑;那么18世纪艾迪生与斯蒂尔的世态人情的幽默讽刺小品使散文的题材风格一变,成为第二个里程碑;至19世纪初多萝西·华兹华斯的自然风景散文风格又一变,开浪漫主义散文的先河;随后至19世纪中叶,兰姆的幽默抒情小品,赫兹利特的杂文,德·昆西的抒情散文分别自成一家;此后大师迭出,加莱尔·安诺德、罗斯金等向社会与文化批评方面发展,最后史蒂文生以游记为高峰,结束散文的浪漫主义运动阶段,是为第三个里程碑;至此,散文取得与诗歌、戏剧、小说同等的地位。(倪庆饩《格拉斯米尔日记》译者序)
尽管倪老师在英国散文方面下的力气最大,但他的视野并不止于散文。他还译过小说,比如史蒂文生的《巴兰特雷公子》。这个史蒂文生,就是写过《金银岛》《诱拐》《化身博士》的那个史蒂文生。译者好像特别喜欢这个作家,翻译、出版了他的三本书。倪老师特别欣赏的作家,还有一个,就是赫德逊了。他前前后后翻译了赫氏的三本散文,除了已经出版的《鸟和人》《鸟界探奇》,还有一本《伦敦的鸟》,译出已有十几年,至今尚未出版,原稿还一直在我手里。这几部书,都是赫氏关于鸟的散文集中最著名、最有代表性的。他也翻译赫德逊的长篇小说《绿厦》。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由大明星奥黛丽·赫本主演,得过奥斯卡奖。他也译过理论著作,柳无忌《中国文学新论》。虽以英国散文为主,但也旁及北美,如爱默生、杰克·迈纳尔、华尔纳等。他还写过一些论文,如《哈代威塞克斯小说集的悲剧性质》《王尔德·〈莎乐美〉·唯美主义》,还有研究翻译史的论文。
他还译过一些英诗,如彭斯、雪莱、济慈、丁尼生的诗。柳无忌、张镜潭编的《英国浪漫派诗选》,压卷大轴,是大诗人济慈的长篇名作《圣安妮节的前夜》,译者也是倪庆饩。
她一边翩翩起舞,眼睛却茫然无神,
呼吸急促,嘴唇流露出内心的焦急
那神圣的时辰迫在眉睫,在铃鼓声中,
在喜怒无常、低语的人群里她叹息
在爱慕、挑衅、妒忌和鄙夷的目光下,
为那飘缈的奇想所迷;除开圣安妮
和她未曾修剪过的羔羊 ,以及朝霞
出现前难以言传的幸福又如此神秘,
在她看来,今宵其他的一切都毫无意义。
因而她打算随时退场,还在夷犹不定。
同时,年轻的波斐罗,驰马飞越荒原,
已经到来,他内心为玛德玲燃烧。
贴紧扶壁,避开月光,此刻正站在大门边,
恳求所有的圣徒来保佑他能见到玛德玲,
哪怕一会儿,他也可以向她定睛注视,
顶礼膜拜,这一切都在暗中进行,
没有人会看见;也许还能促膝倾诉相思,
触摸,亲吻——其实这些事古已有之。
四
倪老师在我读研究生一年级时,教我们英语精读。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第一个年头。秋天,学校开学。那天,我们见到一位老者,步履缓慢,走进教室,走上讲台。他的身材中等偏矮,穿着朴素,大概就是“的卡”布的中山装;头发花白;他走路慢,右腿往前迈时,会先有轻微的一顿,好像句子中不小心多了一个逗号。那步履的节奏,多少年都是那样,慢慢的,一步一顿。
开始那阵子,我只是觉得这位老师讲课有点儿特别。他说话轻声慢语,带着一点儿南方口音。特别的是,一个“公外”(公共外语教学部)的老师教公共英语,却在课上不时地提起王国维、陈寅恪。他似乎对手上的课本并不十分在意,教这些东西,在他眼里好像只是小技,并非学习英文的大道与鹄的;而且,他经常眉头微皱,在那种些许的漫不经心之中,他的眼神和眉宇之中仿佛还有一丝忧愁与伤感。当年的研究生教室里总好像空空荡荡。老师的讲课,我有一阵子都不怎么听得进去,在课堂上经常心猿意马,只盼着何时下课,和当时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想着人生前途之类的大事。
倪老师送我的第一本书,是《英国浪漫派诗选》,时间是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八日。扉页上他写的是:
“给晓风
友情的纪念”
偶尔也会写:“晓风同学存念”,或者:“晓风君存念”,但“友情的纪念”写得最多。落款,有时是他的名讳,有时则是“译者”——这些题签,当时就让我感到与众不同。
倪老师说过好几次,说我跟他认识这么多年,却没有跟他翻译什么东西,遗憾。这于我当然是非常大的损失和遗憾,更是令我非常惭愧。但我也并非没有收获。比如,因为倪译柳无忌《中国文学新论》的缘故,我不但有幸认识了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秦桂英,还认识了她的先生章安琪,他们夫妇也都是南开出身。章先生是研究缪灵珠的专家,当年当过人大中文系系主任。也因为倪老师,我认识了柳无忌,甚至采访了柳先生。朱维之先生是当代中国研究希伯来文学的开创者,也是八九十年代全国高校最通用的《外国文学史》教材的主编。朱维之先生当过中文系系主任。但我认识他,却是通过倪老师的介绍。和百花结缘,也有倪老师的功劳,我通过倪老师认识了百花出版社的谢大光先生、张爱乡,等等。还有,我也是在倪老师家里,第一次用真正的英文打字机练习打字。还有,更重要的是,他给我打开了英美文学的一扇大门。
我为倪老师,当然多少也做了一点事情,于我来说,值得骄傲。当年,一九九三年春天,我到北图,替倪老师把《普里斯特利散文集》借出来,花了一个下午,翻阅、选目,然后复印。出版方面,赖出版社的诸多朋友鼎力相助,东方出版社出版的《绿厦》《爱默生日记精华》,云南的三本书,花城的《格拉斯米尔日记》《水滴的音乐》,还有河南大学的两本书,加上这次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再版的三本书,总共十二本,是我帮着联系的。——这里,我要替倪老师谢谢这些朋友,感谢你们为倪老师做的一切。——我拿到译稿原稿,第一件事,就是到街上找最近的复印店,先把稿子复制一份再说,有时为了需要,要多联系一家出版社,就复制两份儿。总之,给出版社的尽量都是复印件,以确保手稿安全。因为稿子都是手写稿,复印起来比较慢,往往要等两个小时,或者更长时间。另外,倪老师的几篇译后记,也是经我手,在《中华读书报》发表的。
但这些,终究抵不消我心里的愧疚。特别是看到他给我的这些信,翻看他送我的这些书。
倪老师给我的完整的信,现存三十七封。所谓“完整”,就是有信封。还有几页复印的材料,及两三页信,信封找不到了。这样算来,总共有四十多封吧。
晓风:
寄来的报纸与贺年片均收到,谢谢。韩素云的报道虽为配合宣传而写,但能登在头版头条也是成功之作。希望能为文化问题写点专题,这可能是你内行,如学者的生活,前看电视,季羡林先生晚年屡遭家庭变故(夫人与女儿均去世,家里较凌乱),如能写几篇报道,引起有关方面重视,这也是解决知识分子生活的一个侧面,另外稿酬过低问题,盗版问题,这都是热门。记者也是要有专长和专家的,你要去搞工业和农业就费力。
不久前收到花山出版社编辑张国岚的来函,他们想编一套外国游记丛书,对史蒂文生游记加以青睐,想重印,但此事征得百花同意,否则也会引起后遗症。张国岚的信寄到西南村,我想可能会是你联系的。谢大光来我家要稿,赫胥黎文选已被拿走,他问起你,向你致意。我所译史蒂文生小说:《巴兰特雷庄园的公子》(Master of Ballantrae)是他的名著,压在百花已十年。如有便请你介绍中国青年出版社,该社在南大约稿,我不知消息,他们在外文系组了八部小说稿。信息不灵,落后一步。有其他机会亦可,但必须较高层次的出版社。
今年我有两部书发排,Davies: Autobiography of a Super-Tramp,与J.B.Priestley: Selected Prose。但现今稿费太低,且又通货膨胀,实在不利于我们这些搞学术的文人。
你春节可能回家,请代向令尊令堂致意问好。
祝工作顺利
倪庆饩
95,1,24
他在信中所谈,大多都像这样,离不开翻译和文学。他不止一次和我说,也在信中说过,中国现代散文与英国小品文的关系,特别认为林语堂和《论语》派受英国散文的影响,认为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大题目,鼓励我来做。——可惜我限于主客观条件,一直未能如他愿,让他颇为失望。与翻译有关,还有就是他的译著的出版的事情,与出版社的联系,等等。他多次抱怨书稿在出版社一压几年、甚至十几年出不了,出了之后,稿费低不说,而且往往一拖又是一年两年。——当然,他也说他理解出版社的难处,现在出纯文学的书,大多没有销路。——有好几封信中,也都谈到赫德逊《鸟和人》《伦敦的鸟》。
《鸟和人》一书插图
有的时候,他因为头一天打电话我没接,第二天他就写来一封信。——这就是让我现在想来心里就不安、难过的一件事。岂止是现在,就是当时,我心里就满怀愧疚。倪老师打来电话,有的时候固然是我当时不方便接,比如正在开会,或者正在开车;但也有的时候,是我心里发狠,故意不接。我不接,当然也有我的理由。倪老师在电话里,他说的内容,也都是出版书稿的事,其实大多都已经和他说清楚了。他和我一说,就停不下来,半小时,一小时地说——而我又不能很生硬地打断他。即使如此,有时因为我手头儿确实有事情,又只好生硬地打断他。特别是大约二○○六年以后,他打电话,更不能控制。——后来,我静下心来想,明白这是因为老人寂寞,想让我陪他说说话而已。而我呢,在心里确实是有点儿不耐烦。同样,我回天津,回南开也比较多,大概回去三次,中间才去看他一次,而且,往往都是临去之前半小时打电话——因为知道他反正都在家,所以就先到其他地方办更重要的事,有了空当儿,才联系他。——我这点儿小心眼儿,他当然根本不知道,也就无从介意,只要我来了,他都高兴得不得了,拉着我说个没完。——想想,其实我可以多陪他聊几次天的。
还有一些琐事,点点滴滴,难以尽述。他经常批评我的,就是我没有一个研究的主攻方向,他总希望我能多写一些专业研究的文章。二○一○年,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安排我和几位同事十月底去欧洲访问,先到英国,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牛津大学。九月初,我去看倪老师,和他说起来要去英国,他非常高兴,一脸羡慕,说他一辈子翻译英国散文,却没有出过国,更没有去过英国,真是遗憾。让我去了,替他好好看看,回来跟他讲。
倪老师爱书如命,有时也天真得像个小孩儿。他愿意借书给我看,但总是记得哪本书,过一段时间会问我看了没有,看过了就要还他。有一次,我还书时,他对我说,还有一本书没有还。我说还了呀!他一听急了,说没有,他接着说:“你是不是看着那本书好,想不还我了?不行,我跟你去你宿舍去找”。于是,他“押”着我,都骑着自行车,一起从西南村他家,径直赶到我们十七楼研究生宿舍,一起和我爬五层楼,到得我宿舍,居然就从我的书柜里把那本书找了出来。——他那份儿得意劲儿,甭提了,一脸高兴,拿着他的宝贝书,得胜还朝了。
多年以后,我回西南村看他,他把托人从加拿大买的两本英文原版书,赫德逊的Birds and Man和 Birds in London 送给了我,这就是《鸟和人》和《伦敦的鸟》。
五
去年,也就是二○一八年五月九日,我最后一次在天津总医院见到倪老师。他躺在病床上,已经不大认得我了。这次我是陪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两位同志,专程到天津见倪老师,为这几本书的出版签合同。是他女婿代签的,倪老师已经无法和人正常交谈了。但是说到赫德逊的《鸟和人》《鸟界探奇》,他眼里还是有了光,有点儿兴奋。听说再版的书会配插图,他更高兴,呢喃着说,赫德逊的这两本书都是名著,一定把图配好。
我们回到北京后,不到一个月,六月二日,倪老师就走了。又过了一个月,《中华读书报》发了条消息:
著名翻译家倪庆饩逝世
本报讯 著名翻译家、南开大学教授倪庆饩,日前在天津病逝,享年90岁。倪庆饩,1928年出生,湖南长沙人,笔名“孟修”“林荇”。1949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47年开始发表翻译作品,有希曼斯夫人的诗《春之呼声》、契诃夫的小说《宝宝》等。毕业后曾在北京某对外文化交流部门工作,后任教于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外文系,上世纪70年代末调入南开大学公共外语教学部。擅长英美散文翻译,出版译著近30部,在中国翻译史和英美文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发表论文多篇。
倪老师没有什么嗜好,烟酒一概不沾,也不爱喝茶;棋牌也不摸,他觉得那些都很无聊。他工作是翻译,爱好也是翻译;休息就是看书,看林语堂、钱钟书;他喜欢穆旦,推崇傅雷、冯至。他的运动就是一步一顿地去图书馆。可是后来老了,图书馆也去不了了。
几年前,我去看他,那时他的头脑还比较清醒,也显然还有正常的思考能力。聊天中,自然又说到他不久前在花城出版的《格拉斯米尔日记》,我很为他高兴。不料,他却突然冒出一句:“我不想再翻译了。这些都没有什么意义。”
是啊,与生命本身相比,我们所做的这些文字工作,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倪老师一生也没有发达过,晚年则更加潦倒。因为醉心于翻译,他在世俗的名利方面几乎无所得。晚近几年,家里又连遭变故,对他更是沉重打击。在南开园中,他就是一名普通的英文教师,几乎没有人知道有这么一个大翻译家是自己的邻居。二○一五年春节之后,大学里假期尚未结束,我专程去南开一趟,找到校党委副书记刘景泉。我把有关倪老师的一些材料带给他看,说,南开应该认真宣传一下倪老师,他堪称是中国翻译界的劳模,也是我们南开的门面。刘书记真不错,很快找了校报落实。这年五月十五日《南开大学报》就登出一篇长篇报道,韦承金先生写的《译坛“隐者”的默默耕耘》——谢谢刘先生和韦先生。
倪老师的翻译,其实与别人无关,我甚至认为,与什么文学理想、翻译理想也没有多大关系。他就是喜欢翻译,喜欢文学,喜欢优美的文字,向往辽阔清静的大自然,喜欢清新自然,喜欢趣味高雅的精神生活。他是为自己翻译,翻译了一辈子。他以翻译,表达了自我,显现了自我的内心,也成就了自我。
从这个角度说,后人对他的赞誉也好,不认同也罢,都与他无关。但是,这些作品,毕竟留在了这世上,以汉语的形式,在东方世界里传播,这是已经发生的事实。这个事实,将会对一些人的思想,发生一些作用。包括对纯正英语的欣赏,对文学经典的品位的认识,对那些作家优雅写作的传达,还有,告诉我们,世界上除了追逐名利权色,还有一种淡泊超脱的人生追求,那很可能是一种更美好、更符合人性的生活方式。而纯正、优雅和淡泊、超脱,也正是倪老师的精神品质。
二○○六年除夕,倪老师给我写来一封信。
晓风:
今天除夕,身边我放着Faure的“摇篮曲”CD写这封信。(Sophie Multer小提琴)
《绿厦》未能为出版社接受,深为失望,社方未必比高尔斯华绥水平高。《简·爱》也曾多次为出版商拒绝,所以这并不奇怪。上次我以为他们愿意跟爱默生的《日记精华》一同出版,附寄的两本小说介绍,是希望在《绿厦》出版后再为他们续译,结果颇出我意料,因为这两部书只是在我计划中,因我年事已高,能否有精力完成计划自己也无把握。
寄上Dorothy Wordsworth的《格拉斯米尔日记》代序,作者是勃郎蒂姊妹的先驱,是浪漫主义散文的founder,和她的哥哥在诗歌上的建树是密不可分的。她的《苏格兰旅游回忆》写得更好,对苏格兰的湖光山色的描写前无古人。附寄《格拉斯米尔日记》代序,也可发表作为宣传。
我所有的译作都贯彻一个宗旨,即追求自然与人的精神的sublime,假如能有一本选集,集中起来表现,这一点就看得清楚了。从译济慈的The Eve of St Agnes开始。你差不多我所有的译作都有,现在我寄给你一个表,把我认为的这方面的作品,提供给你作为参考。我希望你选编一本这样的书,再配上画(我有一些画册),按这个思路,大概不需要太多的时间,不过有一篇序阐述一下译文的风格最好。
你的《读书不是新闻》缺了小泉八云的那一篇(《遥望小泉八云》)是个遗憾,因为Hearn是把内容与文字结合得最完美的作家之一。
在这样一个时代,我的想法也许不合时宜,但谁说得准呢?“国学”现在又有点吃香,向“超女”叫板,也许当人们吃够了美国的快餐,还是红楼梦里的茶叶羹、香薯饮等是真正的上品。我相信并力行的是伏尔泰的名言:“你说的一切都很好,但要紧的是耕种我自己的园地。”
祝 新年快乐,新的一年内有新的成果
倪庆饩
2006,除夕
现在为了写这篇文章,翻看这些旧信,不禁茫然。这个饩字,读xì,和“戏”字同音,《辞海》上解释这个字有三个意思,一是“粮食或饲料”;二是“赠送”;三是“活的牲口”。《论语》里有:“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倪老师翻译了几十种名著,收获的是清贫。清贫就是上天给他的回报。老实说,我到现在也并不理解倪老师。我大概只能说,他在现实中受压,却从赫德逊、小泉八云、史蒂文生的书里找到慰藉,获得力量和满足。从这一方面说,他离开这个浊世,也未尝不是一种解脱。我们这些人,每天瞎忙,戴着漂亮而僵硬的面具,在滚滚红尘中耗费生命,却找不到生命的价值。相比之下,倪老师一生做自己热爱的文学翻译,倒是幸福的。
《鸟和人》插图
今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将再版倪老师的三部译作。这是他最喜欢的三本书。这三本,都是关于鸟儿的书,配上了精美的插图,真的很漂亮,仿佛鸟儿张开了翅膀。——让鸟儿带他去天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