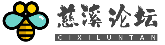《列国志》和别本小说不同。别本多是假话,如《封神》、《水浒》、《西游》等书,全是劈空撰出。即如《三国志》,最为近实,亦复有许多做造在于内。《列国志》却不然,有一件说一件,有一句说一句,连记实事也记不了,那里还有工夫去添造。故读《列国志》,全要把作正史看,莫作小说一例看了。
小说是假的,好做。如《封神》、《水浒》、《西游》诸书,因是劈空捏造,故可以随意补截联络成文。《列国志》全是实事,便只得一段一段各自分说,没处可用补截联络之巧了。所以文字反不如假的好看,然只就其一段一段之事看来,却也是绝妙小说。
《列国志》原是特为记东周列国之事。东迁始于平王,多事始于桓王。而本书却从宣王开讲者,盖平王东迁,由于犬戎之乱,犬戎之乱,由于幽王宠褒姒,立伯服,褒姒却从宣王时生根。且童谣亡国,亦先兆于宣王之世。故必须从他叙起,来历方得分明。此记事人倒树寻根之法,亦不得不然之理也。
《列国志》是一部记事之书,却不是叙事之书,便算是叙事之书,却又不是叙事之文。故我之批,亦只是批其事耳,不论文也。非是我不论其文,盖其书本无文章,我不欲以附会成牵强也。
《列国志》一书,大率是靠《左传》作底本,而以《国语》、《战国策》、《吴越春秋》等书足之,又将司马氏《史记》集采补入。故其文字笔气,不甚一样,读者勿以文字求之。
《列国志》因是集采众书所成,故其事之详略,都是不得不然,当日作者不曾加意增减。若再加修饰一遍,便自然更是好看。
列国之事,是古今第一个奇局,亦是天地间第一个变局。世界之乱,已乱到极处,却越乱越有精神。周室之弱,已弱到极处,却弱而不亡,淹淹缠缠,也还做了两百年天子。真是奇绝。
周室卜世卜年,皆过其数。子孙虽已微弱之甚,而仍称共主,不至遽然亡灭。前人议论,有说周家忠厚开基,盛德之报;有说封建屏藩,互相维制之力。据我看来,两说都有些正,不可偏在一处讲。若说周家忠厚开基,盛德之报,便该多出两个贤王,赫然中兴几次,何以仅拥虚名,丝毫不能振作;若说封建屏藩,互相维制之力,则夏、商两代,建国相同,何以没有许多展转变态?如此论来,则东周列国,还是造物好奇,故作此特奇至变之局,以标新立异耳,不必纷纷强为说也。
由周而秦,是古今变动大枢纽,其变动却自东迁以后起,逐渐变来。其中世运之升降,风俗之厚薄,人情之涥漓,制度之改革,都全不相侔。子弟能细心考察,便是称古大学问。
即如用兵一事,春秋是春秋之兵,战国是战国之兵,不消说是大相悬绝。即春秋中,齐桓与晋文,便有大段不同处。齐桓时用兵,还不过声罪取服,其究竟不过请成设盟而已。到晋文时,便动辄以吞并为事。这便是世变大端中之一小变了。齐桓时用兵,不过论百论千。到晋文时,兵便大盛,一战之际,常以万人。齐桓用兵,还是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到晋文时,便多行诡计了。子弟于此等处能细心理会,便是善读稗官者。
晋文用兵诡谲,却也是到了那个时候,其势不得不然。正是天运改移处,正自怪他不得。若不然,便如宋襄一般,自取祸败了。
用兵之法,变化多端,用少用众,用正用奇,最是不可方物。唯有《列国志》中,却是无体不备。前人于《左传》中,集其用兵计谋,便谓兵谋兵鉴,已得要领,况又益之以战国若干战法乎?子弟理会得此等处,便不枉读了此本稗官也。
用兵是第一件大事,兵法是第一件难事。其中变化无端,即专家也未必能晓彻。今既读了《列国志》,便使子弟胸中平添无数兵法。《列国志》有益子弟不少。
出使专对,圣人也说是一件难事。惟《列国志》中,应对之法最多,其中好话歹话,用软用硬,种种机巧,无所不备。子弟读了,便使胸中平添无数应对之法。真是有益子弟不少。
稽古用兵专对,都是极大极难学问,今却于稗官得之,岂不奇绝。
金圣叹批《水浒传》、《西厢记》,便说于子弟有益。渠说有益处,不过是作文字方法耳。今日子弟读了《列国志》,便有无数实学在内。此与《水浒传》、《西厢记》,岂可同日而语!
一切演义小说之书,任是大部,其中有名人物纵是极多,不过十数百数,事迹不过数十百件。从无如《列国志》中,人物事迹之至多极广者,盖其上下五百余年,侯国数十百处,其势不得不极多。非比他书,出于撮凑。子弟读此一部,便抵读他本稗官数十部也。
《列国志》中,人物情事虽千态万状,无所不有,却无神佛僧道、邪说妖言在内,便觉眼界清净许多,比他本稗官真是好看。
《列国志》中,也有几处说鬼,却是从《左氏传》来,其说鬼处也还在理上,不与他处邪说同也。左氏说鬼,虽与他处不同,然毕竟是他恍惚附会处,未可以为信史。
《列国志》中,有许多坏人,也有许多好人。但好人也有若干好法,坏人也有若干坏法。读者须细加体察,遂各自分出他的等第来,方于学问之道有益,不可只以“好坏”二字,囫囵过了。
《列国志》中,虽也有好人,也有坏人,然毕竟是坏的多似好的,且好人又轻易不能全美。又多是各成其好,不甚相同。至于坏人做坏事,往往如出一辙。亦且穷凶极恶,已精而益求其精的坏法,都坏将出来。当时人君却偏偏欢喜坏人。若善恶同时,又往往好不胜坏。又不知是天意作兴恶人,又不知用人者都是瞎子。真令人解说不出。
坏人明明作恶,还自好辩。偏是大奸大恶之人,他却偏会依附名义,竟似与好人一般,在暗里行其险毒之计。这种人最是难认,观人者不可不知。
恶人依托名义,虽是可以惑人,毕竟也有露马脚处。只要观者不审,便被他所骗耳;若明眼人,自瞒不过。
大约看好人、坏人之法,只从“义利”二字上着眼,便可十得七八。贤奸之变,虽有万态,究其本,总不能外此两字而已。
“义”、“利”二字不并立。天理看得重,爵禄身家看得轻,便是君子;若事事只图自私自利,便自然要行到刻薄险毒上去了,从何处还有天理来。
“义”、“利”二字,其机甚微,到后来便有天渊之隔。即如臣弑君,子弑父,是天地间非常大变。然原其心,却不过从“利”上起耳。若肯将名位富贵看得轻,便自然没有此事了。
《列国志》中,篡弑之祸甚多。其臣为乱臣,子为贼子,罪不容诛,自不消说。然论世者,也要将那君父察勘一番,推求其所以致此之故。虽不以此而宽臣子之罪,却当以此垂戒为人君父者,使其有所畏惮。故圣人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又云:“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又云:“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诸如此类,不可胜数。大率都是互举。后世一切重责子臣,便似凡为君父便可恣肆为恶者,此是宋儒之偏,失圣人之意矣。
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友弟敬,夫和妇顺。自是万古不易之理,亦人情至允之论。然圣人教人,只是自尽。为人父者,只是自尽其慈,不必因慈而遂责子之孝。为子者亦只是自尽其孝,不可因孝而望父之慈。推之君臣、兄弟、夫妇,都是一般。便自然不至有人伦之变。《列国志》中许多人伦之变,总由望于人者深耳。
父以慈而责孝,子以孝而望慈,已是不可;况又有父不慈而专责子之孝,子不孝而专望父之慈。君臣、兄弟、夫妇间,总不自尽,一味责人,岂不可笑。居心如此,安得不做出把戏来。然世又偏多此一辈人,可叹也。
立子以嫡,无嫡立长,自是正理。废嫡立庶,废长立幼,于天理人情自是不妥。然立庶立幼者,爱之也;爱之,必思所以安全之。今悖于情理而立之,后来便必致有杀夺之祸。不特富贵享受不成,反连性命都送断了,又贻家国以覆乱之祸。其是非利害本自显然,却以私心所溺,遂弃安从危,去利就害,自寻祸乱。《列国志》中,此等不可枚举。前车既覆,后车复然,甚有身与其祸,而到后来仍自蹈之者。此等愚人,真是愚得又可笑,又可恨,又可怜。
忠而见疑,信而得谤,自是常事。只看自己所处之地,与所遇之人何如耳。《列国志》中,此类甚多。其中有学有术,处之有方者,庶几自全。若只是一味自信,莽戆行去,个个身受其祸。如申生、叔武之类是也,读之令人时生学术不多之惧。子弟于此等处,须加意理会,万勿草草看过。
《列国志》中,有许多出于微贱,一时投契君心,遂得致位卿相,荣宠终身。如管仲、宁戚、百里奚、范雎等类,其胸中抱负经济,都是最上一流。只看他初见时,各有一番高识定论,足以深入人主之心。至其后来设施,也都是条条件件,次次第第,上利君国,下益民心,可见不是一时取口舌之便者。然若不是机缘凑巧,便也只好困穷草泽,沉埋一生了。天下万世,怀才抱艺而不得其时者,何可胜道,思之令人浩叹。
战国是游士之世。其游说之术,大都不甚相远。只是其中人品,却自有优劣、邪正、高下之不同,读者须自出眼力分别之,莫作一例看了。
物莫不聚于所好。国君好贤,如齐桓便有管宁等诸人,晋文则有狐、赵等诸人,魏文则有田、段等诸人。齐庄好勇,则有殖绰、郭最等诸人。夫力举千斤,射穿七札,亦难得之才,而一时便有多人。可见一切人材,只患求之不力耳,何患无材哉!有国家者,操用人之权而辄曰人材不足,吾不信也。
人主自中材以上,未有不极知国家之需贤共理者。然高爵厚禄,偏难以与君子,而易以与小人。及到有事之秋,却要贤能君子出力,却是急切没处去讨,遂有乏才之叹,岂不可笑。
用贤人君子,原是极便宜事,他却不肯用。小人平日爵禄,也是一般,到有事时,除不能出力,还要卖国求荣,是极不便宜之事。却偏要欢喜他用他,真不知是何等算计。
贪人不顾天理,昧却良心,做上许多坏事,其意不过图终身受用耳。却不知坏却良心,依旧不得受用,枉落千古骂名,有何便宜处?乃前人跌倒,后人偏不晓得把滑,如《列国志》中,乱臣贼子接踵而起,饕餮嗜金,蚺蛇甘鸠,可胜浩叹!
圣人云:“性相近,习相远。”古谚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中材之主得贤臣,则可以为贤君;与奸佞谗谄之人处,则陷于恶而不觉矣。《列国志》中诸君,大半是因臣下以为转移,而其名誉美恶,遂成千古话柄。天下固多中材之人,其尚择所与哉!
人家弟子天性高明,不为俗情所染者,千万中只好一二。其傲狠下流,不可化诲者亦少。大约俱是中材。幼时父师教训,是不消说。到成童以后,若朝夕起作,都是有学问有品行之人,便自然日进于上达。即商贾买卖中,常与老成敦厚者相习,便也可成一个敦朴诚实之器。若于轻薄佻诈浮荡者处,便自然要往下流一路去了。但为善难而为恶易,故常亲善人,未必便善;而不与善者处,便容容易易走入邪径。相与起作之人,十个中只有一、二个坏的,那弟子便有些不可保了。若善恶相参,那一半好人,便全不足恃,况并无贤人君子在内,又何望其向上乎!为人祖、父之心,谁不愿子孙作贤人君子,而不为之择交,是犹南辕而北辙也。及到他已是习于下流,却才悔恨去责备他,要他改过,尚可及邪!
尝论正人最是难交,只是图他有益耳。与不肖处,煞是快意,只是相与到后来,再没有好收场。正人平日事事要讲理讲法,起居饮食,都要色色周到,已是令人生厌。若你做些不合道理之事,便要拦阻责备,使人絮烦。但是与他起作,却也没甚祸害出来,即或有意外之虞,他便肯用心出力,排难解纷,必期无事而后已。不肖之人,平日或图饕餮口腹,或图沾润钱财,随风倒舵,顺水推船,任我颐指气使,其实软媚可喜,只是他到浸润不着你的时节,稍拂其意,翻过脸来,便可无恶不作,从前之快心,都是今日之口实。或遇你有别事,他便架空生波,于中取利,事若败坏,他便掉臂不顾,还要添上许多恶态恶言,不怕你羞死气死。却怪世人择交,偏要蹈软媚洗腆,及到事后追悔,已是无及。试看《列国志》中,君相用人,士大夫交友,往往堕此套中而不悟,可悲可叹。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虽是两句熟话,却是亘古不易之言。试看《列国志》中,许多君相卿士大夫,起初任情径遂,不听好言;无不贻到头之悔。及到祸乱已成,身名已败,却才思想善言,自羞自恨,已无及了。吾愿普天下贤士大夫、读书学者与良朋密戚,逆耳言来,莫便愤然加怒,且将那言语细细详味一番,即使其言不是,于己亦无所损;倘事有可疑,理有足采,便可及时补救,免到后来懊悔也。
本书中批语议论,劝人着眼处,往往近迂,殊未必惬读者心目。然若肯信得一二分,于事未必无当,便可算我批书人于看书人有毫发之益,不止如村瞽说弹词,仅可供一时之悦耳。
教子弟读书常苦,大都是难事。其生来便肯钻研攻苦,津津不倦者,是他天分本高,与学问有缘。这种人,于百中只好一二,其余便都是不肯读书的了。但若是教他读论道论学之书,便苦扞格不入。至于稗官小说,便没有不喜去看的了。但稗官小说虽好,毕竟也有不妥当处。盖其可惊可喜之事,文人只图笔下快意,于子弟便有大段坏他性灵处。我今所评《列国志》,若说是正经书,却毕竟是小说样子,子弟也喜去看,不至扞格不入。但要说它是小说,它却件件都从经传上来,子弟读了,便如将一部《春秋》、《左传》、《国语》、《国策》都读熟了。岂非快事。
有人来说,《列国志》也不是全美之书,不可辄与子弟读。试问其故。则曰:其中夹有许多骄奢淫逸、丧心蔑理之事,恐怕子弟看了,引他邪心。此真三家村中冬烘先生之见,否则假道学及小儿强作解事者也。夫圣人之书,善恶并存,但取善足以为劝,恶足以为戒而已。他本小说,于善恶之际,往往不甚分明。其下者,则更铺张淫媟,夸美奸豪,此则金生所谓其人可诛,其书可烧,断断不可使子弟得读者也。若《列国志》之善恶施报,皆一本于古经书,真所谓善足以为劝,恶足以为戒者,又何嫌于骄奢淫逸、丧心蔑理也哉!《列国志》是一部劝惩之书,只看他忠奸厚薄无有不报,即不报之于身,子孙也终究逃不过。真是有益世道人心不小。
他书亦讲报应,亦欲劝惩,但他书劝惩多是寓言。惟《列国志》中,件件皆是实事,则其劝惩为更切也。
《列国志》中繇词,其语甚古,亦甚验,不知当日所用是何古书?如何古法?自秦火后失传,殊令人恨恨。
《列国志》前后评语,悉是随手写去,更不曾重加点窜,其中字句多有不妥适处。盖我只是评其事理之是非,原无意于文字之工拙也。
《列国志》中,谬误甚多,如《左传》、《史记》,俱言宋襄夫人王姬,欲私通公子鲍而不可。旧本乃谓其竟已通了,又说国人好而不知其恶。此事关系甚大,故不得不为正之。他如彗星出于北斗,主宋、齐、晋三国之君死难,本是周内史叔服之占,却作是齐公子商臣使人占之。此类甚多,不能遍及也。
词曰: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
英雄五霸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
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
前人田地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
乾隆十有七年春
七都梦夫 蔡元放氏题